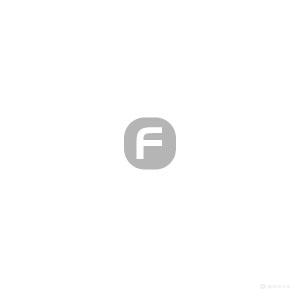人们开发出精妙的技术来制作复杂的图案,既包括织布本身,也包括表面的装饰。锦缎是用补充纬纱编织而成的复杂图案,有多种变体,包括带有额外绑扎经纱的复杂兰帕斯织法。缂丝是一种挂毯编织物,可能最初由中亚人用羊毛纱开发,在宋代(960-1279 年)及以后的中国织工的作品中得到了高度改进。刺绣是一种用穿针引线来装饰织物的手段,在中国丝绸纺织史上一直盛行。
丝绸与外交
绸作为交礼的价很早被人认识到了。公元前三世纪的儒家文献中就提到了这种做法。宋朝 (960-1279) 期间,一些送给边境民族的外交礼物包括 20 万匹丝绸。
公元一世纪,老普林尼在其著作《自然史》(第十二卷,H.拉克姆译,1952 年,第 3 页)中写道:“这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启发……令人惊奇的是,从这些开端开始,人类就开始开山采石、制造大理石、远赴中国制作衣服、深入红海寻找梨子。”
1912 年,奥雷尔·斯坦因爵士 (1862-1943) 描述了在敦煌“被围起来的寺庙图书馆”中发现的纺织品,其中包括一幅大型佛像和菩萨刺绣、一个绣有卷轴花卉图案的绣花垫套、“一些三角形头饰……从彩绘横幅上取下……头饰主体或宽边由细丝锦缎组成”,以及“一个丝绸封面……用于手稿卷”(斯坦因,第 207-210 页)。坦因收集的物现在收在印度德里的英博物和中亚古物博物馆。法国考古学家保罗·伯希和 (1878-1945) 也在敦煌收集了纺织品,现在收藏在吉美博物馆和巴黎国立图书馆。另一批敦煌材料位于圣彼得堡,较新的发现则保存在中国收藏中。
马尼拉大帆船
1453 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扰乱了贸易,欧洲人不得不自己寻找通往亚洲的海上航线。1573 年,马尼拉大帆船首次航行时就携带了中国丝绸纺织品。根据马尼拉大帆船主席安东尼奥·德·莫尔加的清单,西班牙商人购买了:
“成捆的生丝……白色和各种颜色的未捻的细丝……大量的天鹅绒……其他的天鹅绒以金为主体,并绣有金线;编织的织物和锦缎,用金线和银线织成的丝绸……金线和银线……锦缎、缎子、塔夫绸……亚麻布……棉花。(舒尔茨,第 73 页)”
历史和考古证据
在中国最早有人居的遗址中现了针头在公元前千年的遗中发现了大量用大麻和苎麻制作织物的证据。在这些遗址中发现的石制或陶制纺锤轮证实了大麻或苎麻纤维被纺成线用于编织和缝纫。还发现了可能是背带织机的部件。在陶器底部(例如在陕西省半坡发现的陶器)上印有编织材料的痕迹,表明粗布或席子有多种用途,在这种情况下,粗布或席子被用来制作一个简单的陶器转盘。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遗迹证实,公元前三千年就开始了养蚕业。这里有最早证实的证据,证明养蚕( Bombyx mori )、从蚕茧中抽取丝丝,然后缫丝织成布的复杂过程已经发展起来。
 丝绸生产
丝绸生产
商朝(公元前 1550 年 – 公元前 1045 年)和周朝(公元前 1045 年 – 公元前 221 年)
中国青铜时代的墓葬提供了证据,表明丝绸与青铜和玉器一样,是一种奢侈品,对礼仪用途很重要。河南省安阳市的王陵表明,礼仪青铜器和礼仪玉器在作为陪葬品下葬之前都用丝绸包裹。在妇好夫人(公元前十二世纪)的墓葬中,已知有五十多件礼仪青铜器被包裹在丝绸中。安阳丝绸包括各种编织物、锦缎以及平纹(平纹)编织物,有些丝绸上绣有链式针法图案。
战国时期(公元前453-221 年)周代丝的发现令人目,这体现以中国长江游为中心的特周文化。湖北省马山古墓(可追溯至公元前四世纪)出土了以下丝绸:棺盖、丝绸画、器皿袋、木棺人物服饰以及尸体周围的十九层衣物和被子。其中还包括素色丝绸、锦缎、素色和图案纱布以及十字绣和计数针刺绣。对复杂且密集编织的马山丝绸的分析使学者们认为,一定是使用早期的织布机来生产它们。
周文化的其他著名发现证实了丝绸早期作为绘画底料的使用,特别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两面图画旗帜,它们用于葬礼仪式,然后与死者一起下葬。一部被称为“周丝绸文书”的作品可追溯到公元前300 年左右,它记录了早期中国文本写在丝绸和竹子上以及铸在青铜上或雕刻在石头上的传统。这一时期的丝绸上发现了商店标的例子,包括一件带有印章的锦缎,这表明人们越来越尊重独特的作坊产品和纺织品的商业价值。
中国传统边界之外的考古发现证实了早期关于中国向邻国出口丝绸的零散记载。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山脉帕兹雷克的斯基泰人墓葬中(1929 年和 1947-1949 年发掘),发现了可追溯到公元前 500-400 年的丝绸和近东纺织品。这些证据证实了希腊人在公元前五世纪或四世纪进口中国丝绸的信念
秦朝(公元前 221-206 年)和汉朝(公元前 206 年 – 公元 220 年)
秦始皇(因 1974 年发现“兵马俑”而为人所知,21 世纪初)在建立中国第一个帝国后,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宫殿。在宫殿遗迹中发现了丝绸,包括锦缎、绫、素丝和绣花丝绸。在汉朝重新巩固帝国后,丝绸生产成为主要产业,国家监督的工厂雇用了数千名工人,生产绸和皇室服饰。官员有时会得到绸纺织品作为酬或奖励。随该时期末期稳性的下降,纺品和谷物取代了货币,成为公认的交换媒介。
周朝的遗产继续蓬勃发展,这一点可以从湖南省马王堆贵族墓葬(公元前二世纪)出土的丰富宝藏中看出。这里有保存完好的丝绸服饰,包括长袍。此外,还有手稿、地图和丝绸画作,包括精美的丧葬旗帜,上面描绘了死者进入来世的画面,其中有宇宙符号和永生的标志。刺绣丝绸沿用了早期马山丝绸的图案,使用链式针法缝制云卷图案。在马王堆发现的印花丝绸与在南越第二代国王墓(位于广州,可追溯到公元前 122 年之前)中发现的浮雕印章相对应,证实了技术和风格已在整个帝国传播开来。
汉墓出土了各种丝绸,包括平纹、纱织(平纹和花纹)和类似天鹅绒的绒圈织锦。鉴定出二十多种染色颜色。织物装饰括采用金或羽毛绣的新技术,以在丝绸上进行木印刷、模版印刷绘画。后期汉代丝绸包括大量带有文字的编织图案,通常是几个具有吉祥含义的字符。根据图画,学者们推断汉代织工使用脚踏织布机。

湖南某古墓出土汉代丝绸旗帜
在偏远地区的发现加深了我们对丝绸纺织品生产和贸易的了解。奥雷尔·斯坦因爵士在中国西部发现了一条未染色的丝绸带,上面手写着产地、尺寸、重量和价格。印章印记表明其产地是中国东北的山东省。其他发现确定了汉代丝绸的标准布边宽度,介于 17½ 到 19½ 英寸(45 到 50 厘米)之间。斯坦因(1906-1908 年 1913-1914 年)在位于现代中国最西北地区(疆省)塔里木盆地楼兰发掘出土了汉花纹丝绸纺织品碎(可追溯到公元三纪或更早),同时还发现了一件早期用羊毛编织的缂丝织锦。后者可能是后来的丝绸缂丝织锦的前身。蒙古北部诺因乌拉发现的公元二世纪的文物进一步证明了丝绸在亚洲的广泛交流。尽管贸易的细节尚待完全了解,但早期作家的评论清楚地表明罗马世界对中国丝绸的钦佩。
六朝时期(220-589)和唐朝(618-907)
公元三至六世纪期间,政治上的不统一使唐朝与中亚地区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从而产生了与纺织生产相关的新风格和新技术。唐代丝绸反映了前几个世纪建立的这些更紧密的联系。唐朝保持着开放的首都,商人中有外国人,民众中有各种民族和宗教群体。织造技术的普遍转变使代丝绸与汉代丝绸有所区别。汉代的图案是经图案,而唐代的织造案则是纬线图案。
些最好的唐代纺织品存在日本的寺庙中,公元 8 世纪之前,中国纺织品就被精心保存在佛教寺庙中。这些藏品中最重要的是正仓院(756 年在奈良东大寺设立的仓库,用于存放圣武天皇捐赠的藏品),里面有各种服装和其他纺织品,据信这些服装和其他纺织品是由从中国归来的佛教僧侣带回日本的。
中亚地区发现保存完好的古代纺织品,包括奥雷尔·斯坦因爵士在中国西北部和亚洲内陆的探险(分别于 1900 年、1906-1908 年、1913-1916 年和 1930 年),这些发现刺激了人们对中国纺织品的研究。敦煌佛教石窟的发现提供了一系列可供研究的新纺织品,并让人们早期认识到纺织品在佛教仪式中的重要性。这些纺织品可能是中亚(尤其是粟特)佛教徒以及中国佛教徒的虔诚供品许多丝绸被缝制成佛堂的横幅或其他装饰品,或制神圣文本(经卷)的包纸。还发现了一件佛教侣的披风(袈裟),其布象征着贫穷的誓言。多丝绸纺织品都有鲜艳的图案,无论是编织的还是刺绣的,而其他一些则在编织后通过绘画、印刷、模版印刷或使用防染技术(包括夹防染、蜡防染和扎染)进行装饰。这些发现记录的编织技术包括丝绸挂毯 (缂丝)、纱布和锦缎,以及可能在织机上编织的复合纬面和经面织物。这些发现证实,佛教的赞助鼓励了图案纺织品的创作,这些图案纺织品要么用缂丝技术编织而成,要么用高度精致的针法(通常是缎纹针法)进行刺绣,以创造具象效果。
陕西省法门寺曾发现唐代丝绸的重要样本。这里出土的一件可追溯至公元874 年的祭祀用品包括约 700 件纺织品,包括锦缎(许多带有金属线)、斜纹布纱布、春亚纺、刺绣和印花丝绸。其中有一套微型佛教饰,包括袈裟模型、围裙或祭坛前饰)和衣服,全用金线包裹在丝绸纱布上形成莲花和云朵图案。

宋朝(960-1279)
宋代织工将纺织技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缎子和缂丝织锦的织造。一般来说,金银在刺绣和织锦中的使用都越来越多。针环绣开始流行,这是一分离的环状针法,有时与金纸贴花相结合。在宋代和唐代,刺绣和缂丝被用于制作佛教图像,但现在这些技术也被用于制作用于审美欣赏的物品,如卷轴或册页形式的绘画。
金朝(1115-1234)和元朝(1279-1368)
在金朝和元朝(金朝由鞑靼人女真建立)统治下,丝绸在贸易、外交和宫廷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金朝和元朝均由蒙古人建立,而这两个王朝都不是中国统治王朝。金和元锦缎以用皮革或纸质基材镀金的纬纱制作的丰富图案而闻名,是最近展览的焦点。由于蒙古征服鼓励了开放的贸易联系,这些丝绸传播广泛。一些丝绸通过贸易和外交礼物传到了教皇手中。因此,蒙古领导人青睐的金布在14 世纪欧洲的panno tartarico中也有对应物。
明朝(1368-1644)
到了明朝,织工们使用精巧的织布机,使用多达四十种不同颜色的纬线,并加扁平的金条(镀金纸)、金线以及彩虹色的孔雀羽毛来制作锦缎。永乐朝(1403-1424 年)投入量资源制作外交礼物,包括于佛教目的的纺织品,这种法一直延续到宣德朝(1426-1435 年)。在明朝皇帝万历皇帝(1572-1620 年在位)的陵墓中,发现了两套完整的未切割的丝织龙袍,以及丝绸锦缎和图案纱布,这些丝绸锦缎和图案纱布被标记为南京和苏州皇家作坊的产品。
到 16 世纪末,棉花种植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朝鼓励种植棉花,明朝进一步扩大种植范围。至少从唐朝开始,棉花就被用来为下层阶级制作衣服(卡希尔 [p. 113] 指出,“穿棉衣”在中世纪中国诗歌中意为平民)。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棉布与谦逊的美德联系在一起。轧花棉从河南和山东省向南运输,或从福建和广东向北运输到江南地区,在那里制成棉线并织成布。棉线是中国出口到日的商品之一,白色棉布以及蓝色或白色的棉质服装也是马尼拉大帆船出口的商品之一。
在国内,花被广泛用于内衣和丝绸衬里例如用于仪式的丝绸服装),且它还被染成鲜艳的颜色并压成美观的抛光表面。中国棉纺织品最独特的艺术发展主要存在于农村传统和少数民族民间艺术中,包括贵州和云南省的苗族。主要技术,防染(使用模板涂抹糊状物以保留白色未染色区域)和蜡染(使用蜡保留未染色区域)自汉代以来就已在中国为人所知,还有木版印刷、扎染和夹染,这些技术在唐代保存下来的丝绸样品中也有发现。靛蓝特有的蓝色是染色棉的典型特征,也反映了明代文献中详细记录的古老传统。
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注意到,十七世纪中国女性的重心从织布转向刺绣。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成品纱线和成品布料可以定期购买。这激发了士绅对刺绣的趣,刺绣的地位也随之上升,接近绘画和书法等美术。例如,上海顾氏家族因其独特的图案刺绣风格而声名鹊起。学者书法家沈林启(1602-1664)编撰的刺绣图案手册以木刻版画形式出版,其中列出了几个世纪以来激发刺绣灵感的主题和图案。
清朝(1644-1911年)
清代纺织品研究主要集中于宫廷藏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包括墙饰、窗帘、案头饰和室内装饰织物、礼服和便装以及艺术品。乾隆皇帝受到晚明文人收藏家以及宋徽宗(1101-1125 年在位)先例的启发,委托文官编目其艺术藏品(产生了《璧殿竹林》和《石渠宝笈》,分别出版于 1744-1745 年、1793 年和 1816 年),这些目录中除了绘画和书法外,还收录了缂丝和刺绣的样本。乾隆本人可能已选择了一些作品以缂丝“复制” ,包括他自己的绘画和诗歌以及他收藏的书画作品。
清朝皇帝是满族人,他们的故乡位于中国传统边界之外的东北地区。当他们服中国后,他们迅速采用了国的做法,即用丝绸(尤其是龙布料)作为礼物,将藩属国的强领导人拉入自己的军事官僚机构清朝的先辈在明末时期就一直受到这种做法的影响。丝绸长期以来一直被用来安抚边境人民;宋代的例子引人注目,但这种做法早在汉朝之前就开始了。在 21 世纪幸存下来的纺织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赠送给西藏贵族的奢华丝绸锦缎,直到最近几年,这些锦缎才在西藏干燥的气候中保存下来。

织品的收藏与研究
直到最,对中国纺织品的研究都围绕着北的皇宫展开,这是 1911 年清朝统治结束后研究中国文化的焦点。在 1925 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之前的几年里,许多宫廷服饰和其他纺织品分散在世界各地收藏中。西方学者通过这些宫廷长袍和室内陈设了解中国纺织品,对中国纺织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近年来,巴黎亚洲纺织品研究和文献协会 (AEDTA)、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香港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菲尼克斯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学院和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开展的研究对藏品进行了技术分析和历史记录。
另请参阅 中国:服饰史;丝绸。
参考书目
阿诺德,劳伦。《王室礼物与教皇宝藏:方济各访华及其对西方艺术的影响,1250-1350 年》。旧金山:Desiderata Press,1999 年。
Bray, Francesca。《技术与别:晚期中华帝国的权力结构》。伯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7 年。
布鲁克,蒂莫西。《快乐的困惑:明代中国的商业与文化》。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8 年。
布朗,克劳迪娅等。《编织中国的历史:艾米·S·克拉格的中国纺织品收藏》。展览目录。菲尼克斯:菲尼克斯艺术博物馆,2000 年。
Cahill, Suzanne。“‘我们的女人表现得像外国人的妻子!’:西方对唐代女性时尚的影响。”《中国时尚:东方与西方相遇》。由 Valerie Steele 和 John S. Major 编辑。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9 年。
赵峰。《丝绸珍品:图说中国丝绸艺术史》。香港:ISAT/Costume Squad Ltd.,1999 年。中英文版。
Hanyu, Gao。《中国纺织品设计》。Rosemary Scott 和 Susan Whitfield 译。伦敦:Viking,1992 年。
Jacobsen, Robert D.皇家丝绸:明尼阿波利斯艺术院的清朝纺织品。芝加哥:艺术媒体源有限公司,2000 年。
Komaroff, Linda 和 Stefano Carboni 编。《成吉思汗的遗产:1256-1353 年西亚宫廷艺术与文化》。展览目录。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2002 年。
Kuhn, Dieter。“商代的丝绸作坊(公元前16-11 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探索:中国文学和历史论文集特刊》。李国豪等编,第 367-408 页。上海:中国古典出版社,1982 年。
Ledderose, Lothar。《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块化和批量生产》。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 年。
夏乃。《汉代中国玉器与丝绸》。由 Chu-tsing Li 编辑和翻译。堪萨斯州劳伦斯:斯宾塞艺术博物馆,1983 年。
黄能富主编。印染织绣。《中国美术全集:第三部分-工艺美术编》。第6 卷和第 7 卷。北京:物出版社,1985 年和 1987 年。中。
濮璐。中国靛蓝蜡染图案。北京: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1。
Riboud, Krishna。《敦煌丝绸》。《中亚艺术:吉美博物馆的伯希和藏品》。Jacques Giès 编辑,第 115-120、155-164 页。巴黎:Serindia 出版社,1996 年。
Schurz, William。《马尼拉大帆船》。纽约:EP Dutton,1939 年。
Steele, Valerie 和 John S. Major。《中国时尚:东方遇见西方》。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9 年。
斯坦因爵士,马克·奥雷尔。《沙漠华夏遗迹:中亚及中国最西部探险的个人叙述》。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12 年。重印,纽约:B. Blom,1968 年。
香港市政局、香港东方陶瓷学会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出版。《天绣罗衣巧天工:中国纺织千年史》。展图录。香港:香港艺术馆,1995 年。中英文对照。
沃尔默,约翰,等。《衣冠楚楚:芝加哥艺术学院的明清纺织》。展览目录。芝加哥艺术学院。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0 年。
Watt,James CY 和 Anne E. Wardwell,Morris Rossabi 撰文。《丝绸曾是黄金:中亚和中国纺品》。展览目录。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97 年。
Wilson, Verity。《中国服饰》。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1987 年。
声明:服饰易汉服所有文章,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本站原创发布。任何个人或组织,在未征得本站同意时,禁止复制、盗用、采集、发布本站内容到任何网站、书籍等各类媒体平台。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我们进行处理。为了能让本站持续长久的更新下去,大家可以赞助一下本站。